
日月星宿,山川河流,钟灵毓秀,玄石天成。
砂壶之形态美在于对称与均衡,在于比例与尺度,在于对比与和谐,玄石呈与观者一副钟灵毓秀之大景观,一种视觉上之大惊艳,是禅书禅画中的空灵,是返朴归真后的天真,有轻岚淡施,遥山远水之澄静悠扬,亦有风拂杨柳,雨打浮萍之似静欲动。
作品气韵清奇,色泽光润如玉,恰若历经岁月、潺潺流水中自然生成之玄石。壶盖光滑平整,壶嘴微微上翘,再按以一枚小巧卵石为壶钮,破除了壶身圆钝敦重的呆板,使其具有了顿挫起伏的韵律感与跌宕感。作品之线与面、面与面之交接过渡颇似怀素之草书,行云流水了然无痕。杯形各异,杯口或大或小,或侧或倾,朴而不俗,拙而不笨,个个圆润可爱。整件作品在不对称之间形成完美的均衡感,在比例与尺度间造就恰好的宜人感,在对比中达成整体的和谐感,丰肌秀骨,意境曼妙,是砂壶中又一佳品。
不属白昼,不属暗夜,不惹俗世一点尘。
不属暗夜,不属白昼,本是天外物,不惹俗世一点尘。好比想象中的世界,有四季不败的花,有终年不散的云,有迷失的森林,创作者的想象天马行空,大开大
阖,呈给观者一个奇幻瑰丽的作品---天陨。
作品颠覆了传统的创作思路,剑走偏锋,制作手法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传统,表现手法独特大胆又不显夸张。壶身呈不规则椭圆,丰韵饱满,流畅天然,像是信手抟出,但又可经由无穷推敲。壶把立于壶面,看似一圆满的环,壶嘴微凹,不易察觉,流不似流,把不似把,是此壶最别具一格处。作品整体均由曲线构成,线条流畅若溪涧流水,蜿蜒动人,极具节奏感与韵律感,富有强烈的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。各部位衔接自然流利,比例和谐恰当,处处渗透出奇思妙趣,其中之亮点依旧是绞泥灵活肆意的运用,全画面的铺张,绵密与疏朗处理得恰到好处,若龙蛇矫捷,又如烟雾妖娆,色彩之变幻鲜妍,又若春之芳草,夏之初荷。
作品风格鲜明,想象奇突,在砂泥的天然性和可塑性中,融入创作者自身的意趣与情感,以陶的方式表达,以陶的语言诉说,最终表达了创作者想要表达的,完美的完成了这件妙趣横生的作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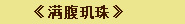
只知外貌之粉泽,谁料满腹填珠玑。
作品轮廓鲜明,色彩绚丽,比例协调,线条流畅,装饰虽繁却无丝毫累赘,极具美感,于视觉而言,无疑是一场饕餮盛宴。古语有云,“囊括万殊,裁成一相。”即是说,把天地万物的精神和形态,都高度概括在“点”和“线”之中。制作者对于点、线运用娴熟,在方与圆,曲与直之间宛转自如,整件作品由线面融合构成,精致细润,和谐统一,转折轻巧利落,弧度流畅优美。
“一杯宽幕席,五字弄珠玑。”(唐.杜牧《樊川文集》)壶体、壶盖
作品颠覆了传统的创作思路,剑走偏锋,制作手法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传统,表现手法独特大胆又不显夸张。壶身呈不规则椭圆,丰韵饱满,流畅天然,像是信手抟出,但又可经由无穷推敲。壶把立于壶面,看似一圆满的环,壶嘴微凹,不易察觉,流不似流,把不似把,是此壶最别具一格处。作品整体均由曲线构成,线条流畅若溪涧流水,蜿蜒动人,极具节奏感与韵律感,富有强烈的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。各部位衔接自然流利,比例和谐恰当,处处渗透出奇思妙趣,其中之亮点依旧是绞泥灵活肆意的运用,全画面的铺张,绵密与疏朗处理得恰到好处,若龙蛇矫捷,又如烟雾妖娆,色彩之变幻鲜妍,又若春之芳草,夏之初荷。
作品风格鲜明,想象奇突,在砂泥的天然性和可塑性中,融入创作者自身的意趣与情感,以陶的方式表达,以陶的语言诉说,最终表达了创作者想要表达的,完美的完成了这件妙趣横生的作品。
只知外貌之粉泽,谁料满腹填珠玑。
作品轮廓鲜明,色彩绚丽,比例协调,线条流畅,装饰虽繁却无丝毫累赘,极具美感,于视觉而言,无疑是一场饕餮盛宴。古语有云,“囊括万殊,裁成一相。”即是说,把天地万物的精神和形态,都高度概括在“点”和“线”之中。制作者对于点、线运用娴熟,在方与圆,曲与直之间宛转自如,整件作品由线面融合构成,精致细润,和谐统一,转折轻巧利落,弧度流畅优美。
“一杯宽幕席,五字弄珠玑。”(唐.杜牧《樊川文集》)壶体、壶盖
均点缀圆圈图纹,星罗棋布,疏密有致,看似随意,却是一一恰好,恰似满腹珠玑,又隐喻优美文章。观其形,取其意,实是匠心独具,且富涵深厚的中华文化气息。紫而不姹,红而不嫣,绿而不嫩,黄而不娇,泥色之暗然,衬以色彩之斑斓,对比鲜明,顿生华美之感。壶嘴探出,壶钮俏挺,壶把端凝,壶足以云纹装饰,以凌云之姿顺势托起壶体,高瞻四方,形成一种视觉张力,一种跳脱的空间感,砂壶之形态美终在此显山露水,出神入化。

古风拙韵,浩气长存
紫砂的特质是“纯”与“净”,趋向于玉石的鉴定规则,要无杂质、无瑕疵。天笠壶杜绝绮丽颜色,一宛一转均为天然,看似平淡,实则情感浓酽意象端凝,有朴素的东方美学理念贯穿其中。
天笠壶取材主题为古时斗笠,古风盎然,造型冷静、自省、端庄,布局整体性的把握娴熟到位。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新突破,圆中寓方,方中有圆,揉和方的刚烈与圆的柔润,达到视觉上的调和。壶钮至壶盖至壶体,运用凹凸与虚实的对比来营造一种层次感、立体感、灵动感。壶身呈圆体,壶嘴胥出自若,壶把探出有力。简洁端庄的风格一气相承自始至终,气韵的洒脱与酣态流于壶面一览无疑。壶把的处理亦是传统理念与创新精神的结合,以蜿蜒姿态延展,中途宛转出优雅棱角,再
古风拙韵,浩气长存
紫砂的特质是“纯”与“净”,趋向于玉石的鉴定规则,要无杂质、无瑕疵。天笠壶杜绝绮丽颜色,一宛一转均为天然,看似平淡,实则情感浓酽意象端凝,有朴素的东方美学理念贯穿其中。
天笠壶取材主题为古时斗笠,古风盎然,造型冷静、自省、端庄,布局整体性的把握娴熟到位。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新突破,圆中寓方,方中有圆,揉和方的刚烈与圆的柔润,达到视觉上的调和。壶钮至壶盖至壶体,运用凹凸与虚实的对比来营造一种层次感、立体感、灵动感。壶身呈圆体,壶嘴胥出自若,壶把探出有力。简洁端庄的风格一气相承自始至终,气韵的洒脱与酣态流于壶面一览无疑。壶把的处理亦是传统理念与创新精神的结合,以蜿蜒姿态延展,中途宛转出优雅棱角,再
以强势姿态收尾,给人耳目一新之体验。
天笠壶为大壶,大,本身就是一种气度,一种浩然,一种扩张,作品把力度作为主调体现,且以厚实的思辩容量为内涵,再加以创作者自身的饱满情感,令作品充满艺术之美,厚积厚发,笔笔有妙意,处处见大气。
天笠壶为大壶,大,本身就是一种气度,一种浩然,一种扩张,作品把力度作为主调体现,且以厚实的思辩容量为内涵,再加以创作者自身的饱满情感,令作品充满艺术之美,厚积厚发,笔笔有妙意,处处见大气。
苍茫天水间,翠的是杨,绿的是柳。
凭栏远眺天水间, 青云浮遮半片山, 一行飞雁穿帆影,绿树琼花染江南。星云之媚丽,山河之秀美,在艺术家眼中,均可入诗,均可入画,均可入壶,天水间壶表现的是如诗的旷达意境,创作者以自身的文学沉淀及和谐的装饰手法,用手工艺术对诗歌进行了完美的诠释,令观者观壶如同读诗赏画般有一咏三叹之感。
作品展示给观者的既有形态美又有意境美,更有两者合而为一的艺术美。用传统的手法造型,辅以绞泥的手法装饰,壶体呈碗状,上部略收,高跨度的金属提梁横架上空,提梁把饰以绞泥,五色混淆,纹理清晰,翻滚涌动之感跃然而出。绞泥手法之随意自然、沉朴淳厚,更在壶体的装饰上体现淋漓,用朱砂色细纹绞出波浪,配合大写意的手法,展现出烟波浩淼之深远意韵,长天一色之磅礴大气,形态、意境丝丝调和,得简约之精髓,具艺术之深美。
作品洗练而不加修饰,含蓄而不流于拘谨,形态舒展简洁,轮廓线条之起承转折一气呵成,着色分外润艳,是在浓厚的人文、巧妙的构思与娴熟的工艺有机结合下的完美之作。
绿浓成阴,渡头涉水,一种闲情,一曲《升平乐》。
绿杨阴下古溪边,日暮碧云芳草地,渡水穿云步步随,手把芒绳无少缓。好一派明媚的田园风光。作品基调明朗轻快,充满童真童趣,隐然有陶潜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之写意。
火与土是陶的语言,没有生命的泥土,注入创作者的思想,便有了灵魂。该作品象形取意,肇于自然,壶钮是一个敦肥的牧童,脚板朝天手托腮,神情似笑非笑,憨态可掬,壶身呈扁圆形,壶嘴似牛嘴微突,壶把似牛尾轻轻扬起再卷曲,在似与不似、像与不像之中,把中国传统美学之意境表现得酣畅淋漓。壶身、壶把、壶盖、壶嘴、壶的线条流畅,弧度饱满,宽一分不可,窄一分不可,长一分不可,短一分不可,各部件搭配匀亭,比例合度,给人视觉上一脉到底、熨贴舒畅之感受。壶体饰以绞泥,手法纯熟精巧,色彩润艳,青翠若琅轩竹,橙黄如怒放葵花。线条清澈明晰中又生万千变幻,曲曲折折,牵牵连连,恰若水波之柔软无常,紧扣主题,直接点出“渡水”二字,一人,一牛,一湖烟波,令观者仿佛身临其境。
作品整体风格平和幽远,略带古朴之风,闲适之意,体现出制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,亦体现出紫砂壶形态美之主流“古朴雅拙”。
高山流水觅知音,余韵一生守望。
巍巍乎志在高山,洋洋乎志在流水,高山流水琴三弄,余韵一生守望,伯牙破琴为子期的古老传说,千年流传,而在千年后,高山流水关乎的是一把壶,一把可以用瑰丽的音符来注释的壶。
对艺术而言,越是传统的,就越有艺术的感染力与穿透力,作品结合了五千年的华夏文化,将传统与创新溶于一炉,再融入创作者自身独有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,观赏此壶,仿若在倾听一阙高山流水的妙音,古声古色,韵味悠长。壶体为扁圆形,色泽温润如玉,线条俊逸洒脱,一气贯通,便如乐章之主题,节奏感优美,韵律感灵动。壶面上隐约浮出如云缎水波之绞泥纹,色暗暗生,恰若如歌的行板,音渺渺而意切切。壶嘴突破传统,形似乍开的半颗莲蓬,构思奇巧,便似乐章之变奏,一波三折,出人意表。乐章的高潮落于壶盖,壶盖平整契合,绘以浓烈的色彩及格纹,与整体淡黄的底色形成强烈对比,予人惊艳之视觉印象。大胆创新的壶把即是乐章之结尾,凌空俏挺却又在末端突地收回,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音符,意犹未尽,余音不绝。
海上旭日,心中净莲;杳远大地,悠悠云天。
天地相隔,本无交集,而水接天连地,合二为一。波光粼粼的海面上,红日初升;晨曦中,一朵净莲正悄然绽放。大气磅礴之中蕴涵静谧幽雅,可见表现功力之精深。整个作品融天地于一体,汇自然于一心,触人心扉,耐人回味。
手法纯熟的绞泥技艺,用简约凝练的笔触于壶身上描绘出云海苍茫之势,使作品恢弘壮丽,韵味悠长。壶钮是一支欲放的荷花,于天水空灵的意象中显得尤为醒目,点缀壶上,使得作品更加气韵生动,生机盎然。提梁如云天,简单的线条营造出寥廓高远的景象,与壶身形成天地一派之势,意境深远。
作者在感悟自然和生命的瞬间捕捉灵感,将情境与艺术巧妙结合,化静为动,物我相融,让整个作品焕发出自然与生命的勃然生机。
矫龙飞天,或曰在渊;紫气浩瀚,一览江山
汉朝刘向在《列仙传》中写道:“老子西游,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,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。”紫气东来,意为紫气自东而来,喻祥瑞。创作者以独特的视角,结合美丽的民间传说,配合独树一帜的制作手法,使作品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。
作品轮廓周正,比例恰当,线条挺括,造型既稳重又挺秀。采取天然泥色,呈墨紫,光华暗显,似有铄铄之光。壶身圆弧润泽,线面渡接自然,壶嘴顺壶身弧度而出,与壶盖、壶把相协调呼应,不落做作之痕,不着雕凿之迹。壶体采用绞泥作为装饰,模拟出云海翻腾、涌动变幻的动态,气势恢宏,意韵悠长,且线条清晰、色泽鲜艳,具有强烈的动感美、气度美及艺术美。
作品的精彩之处、点睛之笔是壶钮,只见壶盖上盘踞一头面目倨傲、蓄势待发的瑞兽,腰微弓,足后蹬,乱石中,山岗上,顿感强风阵阵,草木皆惊!逼真形态,跃然眼前。
作品形、神、气融会贯通,于创作中溶入泱泱华夏文化,兼顾了传统与创新,构思奇巧生趣,做工细腻严谨,设计独特出众。
古风氤氲,心心念念;卓然挺拔,风采弥新。
艺术的高境界是抛弃芜繁最终达到简之又简,这把追古提梁壶未经过任何的装饰与敷染,若初生婴儿般出尘无垢的展示于观者面前,深具素器之原始美,令人赏心悦目。作品造型在继承传统壶型的基础上略加修改,点、线、面巧妙渡接,精致细腻。壶身圆润饱满,轮廓柔和,色泽细润如玉,壶嘴胥出自然,壶钮为一拱形半圆,壶口、盖严密平整,各部件与凌然架空的提梁形成完美的虚实对比,构架清晰,美感丰富迭出不穷。砂壶形态美之欣赏中最重视的线条,亦被运用得纯熟轻巧、张扬有度,走势就若流水行云,富含书法行书的笔意,似在漫不经心中游走,却又透出严谨的法度。作品整体风格柔和明朗,古意盎然,深得传统素器的制作要领,深得砂壶“简约之美”的精髓,于朴实无华中透出静逸与虚空之韵味,于简练中蕴涵高雅的意境。
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着力于创新,根据紫砂最本质的特性,发掘出其自身具备的最天然独特的美,于古风朴朴中渗入现代的气息,赋与作品深厚的内涵及强劲的艺术生命力。
壶谓为《菩提》,取寺之名,摄莲之形,借“尘中修,修中悟,悟中觉”之意。
无量佛如莲,无边佛如莲,人生亦如莲,《菩提》壶则处处生莲。壶体丰润优柔,形若莲瓣。壶颈以浮雕手法饰以花萼,层层绽放,立体感跃然而出。壶嘴探出,有轩昂之态,是摹莲枝旁逸斜出之姿。壶把故作突兀,状若不经,却生动体现出莲茎枝枝节节之态。壶钮精彩迭起,拟为二态,一作圆钮,圆润小巧若莲子,二作花苞,将绽未绽似菡萏。作品点点细琢,处处精致,线条明晰,流、身、把过渡流畅,造型的起势与力度均具艺术美。佛在壶心,衍生为莲,至净至纯,以紫砂独特的材质与视角体现出的森然之美,近乎了禅。 此壶可做大、中、小三款。
口中吃得清和味,身上常穿百衲衣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,几千年悠悠岁月积淀了浓厚的佛教文化,也积淀了无数的民族瑰宝,紫砂尤为佼佼。顺治皇帝早有《赞僧诗》云,口中吃得清和味,身上常穿百衲衣。百衲有佛意,是清朴,是明彻,是无欲求,万丈红尘均可在磐钵木鱼与佛号声中纷纷零落。
作品为圆器,线条走势圆润柔和,转圜流畅自然,选料精究细致,砂粒细腻含而不张。绞泥的运用分外娴熟,宛若信手拈来,或海棠红,或琅玗翠,色泽纷繁绚丽,纹理清晰,对比强烈。嘴、把、盖的比例匀亭和谐,伸探角度适宜精巧,壶体敦实,壶盖平整,壶面绞泥的装饰既丰富了整体内容,又把百衲衣零碎布块的性状摹仿了十足。壶钮的设计也饶有趣味,是一僧帽,理趣结合,形态栩栩。
作品择名百衲,以佛文化为基调,结合紫砂泥料特性,令观者观壶如观佛,感受壶的优雅与敦重的同时亦能领受佛的感召与熏染。
“奥运情”壶以奥运为创意起点,以华夏文化为创意支撑,处处见奥运精神,点点赋中华文化。壶体拟奥运奖杯形状,荣誉感与运动感显而易见;壶之材质,根本连接中国,紫砂之唯一故里;壶之神韵,稳重岿然,端庄优雅,通体显露英姿勃发的民族气节。
壶体造型落落大方,底座夯实,嘴、把处流畅呼应,有中国传统造型中的对称和谐之美。壶体点缀中,线条收放、小品配合、颜色搭配,皆妥贴而有情致,流露出深情的中国人文气息。整个“奥运情”壶,于和谐与灵动之间,传递 “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”的自信和勇气。
壶沿宽阔平整,以圆润曲线勾勒出五大洲的和谐共处,若浑圆地球的一个切面。柔润圆滑的圆曲线,平整若绿茵场上呐喊声四起的环形跑道,奥运会的现场恍若近在咫尺;大手笔拓开的平面,又若历史悠久,地大物博的中国,丰饶的土地上草长鹰飞,生机盎然;不断使用减法的平面,不发一言却思绪万千,用素净的紫砂语言重复一个五洲共鸣的声音:“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梦想”。整个壶身,无一处奥运,却无处不奥运;无一点笨重,却点点显厚重;壶体雍容大方,显示不凡的传统文化底蕴,中华文化的包容并蓄,含蓄内敛,继往开来尽寓其中。
壶盖至壶纽处层层递进,意境渐深渐远,耐人寻味。壶纽状似北京的天坛,由初升的旭日冉冉托起,若蛟龙腾渊,鹰隼试翼,气势蔚为大观,象征着中国如日中天、从无间断的顽强、拼搏与奋斗精神,也对奥运会上更优秀的成绩给予厚望。天坛饰以绛紫色,下承大红色,将“九州生气恃风雷”的豪迈,一一交代。


















